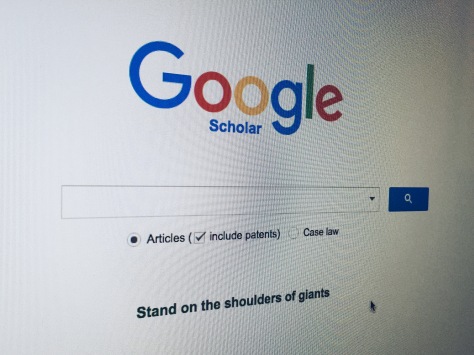樓盤名稱浮誇俗氣,並非甚麼新奇事。樓盤就是一個商品,銷情不好隨時有員工要「人頭落地」。然而近年樓盤建築一式一樣,marketing部門要為樓盤改一個別開生面的名字來吸引買家的注意力,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而改名幾條橋不外乎食字、扮豪氣、刻意用一些要查字典才懂讀音的字等等。近一、兩年亦有一些樓盤,如「帝峯.皇殿」(The Hermitage)和「影岸.紅」等,以「間隔號」發明一個仿似出現在文藝作品中文譯本𥚃頭的名字,以抬高樓盤的文藝氣息。雖然某些業主心知肚明此等名稱的俗套和造作,但總會在寫地址的一刻,獲得一絲的滿足。這就好像陳年在我們書櫃的幾本狄更斯和紅樓夢一樣,可以補償一下我們對於文化生活的空虛和無力感。明知道自己沒有興趣看,但總要買幾本當傢私擺設一下。
圖:Bohemian House,扮嘢到起雞皮。Bohemian又點會有層樓? 揸住層樓又點Bohemian?
這些樓盤名字出現之前,往往只有一個門牌名和土地編號,或甚至只是一個內部專用的working title。幾個字母和號碼串起,成為了建築作品的代號。這個代號只是一個序列號碼,方便內部員工溝通。冷冰冰的編號背後,是講求效率和經濟利益的生產缐。建築師測量師工程師各施己任,流水作業形式的樓盤生產線,沒有任何空間可以講概念、講感情。灣仔利東街重建項目,幾年前提出以「囍歡里」命名,亦向公眾説明會重新引入有關嫁娶的行業的名鋪,以補償當初摌平囍帖街的工程,對社區環境和傳統文化的破壞。雖然,「食字」樓盤名稱確實有一點低章,但起碼有意圖修補受工程破壞的傳統行業,營造高級版的囍帖街,尚算對於社會有點承擔。
然而,所謂「過左海就神仙」,當初的承諾致今並沒有兌現。更甚者,那只是一個過關的手段。據媒體所講,至今的租戶都是時裝和食肆等,發展商亦未有指示要特別邀請嫁娶行業的商戶進駐。似乎由始至終,發展商都沒有認真看待公眾的意見。一個市建局有份參與的項目,竟然比私人發展商更冷血,更無情,眼睜睜的欺騙公眾。在任何的一個建築工程,公眾都是持份者,有權去為自己的城市和社區的面貌發表意見。今時今日,香港不少人都受過高質素的教育,有能力判斷事非。因此,他們的意見和想法一定要得到尊重,而非將他們草草地愚弄過去就可以了事。或者今次囍帖街項目可以過關,但是此先例一開,公眾對於發展商的信任一定再次大打折扣。下一次再有類似的項目和爭議,發展商和市建局遇到的阻力一定大增。為了一步棋而輸掉一整盤棋,賠上整個行業的信譽,值得嗎?
圖:Wikipedia
在公共項目,這個矛盾就更加明顯。政府作為推展工程的一方,卻經常以發展商的模式運作,諮詢過程和獨立評估往往敷衍了事,完全沒有打算認真考慮公眾利益和意見。政府以這種心態操作基建項目,最後引來司法覆核等官司,著實是自己招來的,而非社會大眾刻意阻撓。政府不能夠以發展商的思維去執行公共建築及基礎建設項目。其實建築師的專業角色,就是要平衡各方的利益,以獨立的身分作出協調。要做好和公眾的溝通,大可以專業建築師作為橋樑角色,以獨立的身分(而非政府或發展商一方的僱員)向公眾解釋設計和發展項目,誠心說服公眾而非敷衍了事,這樣才是真正的凝聚共識。在英美等西方國家,這個做法早已習以為常,亦是高度發展的城市中不可避免的趨勢。香港早已脫離需要快速城市化的時代,我們是時候要犧牲一些時間和效率,去好好投資一下城市環境的質素。如果我們城市繼續依賴俗氣空泛的名稱和口號,而不好好思考建築空間和公眾的關係,城市只會淪為一個空殼沉淪下去。甚麼競爭力和宜居度排名,亦只會每況愈下,最後甚至連一個內地二三線城市也不如。